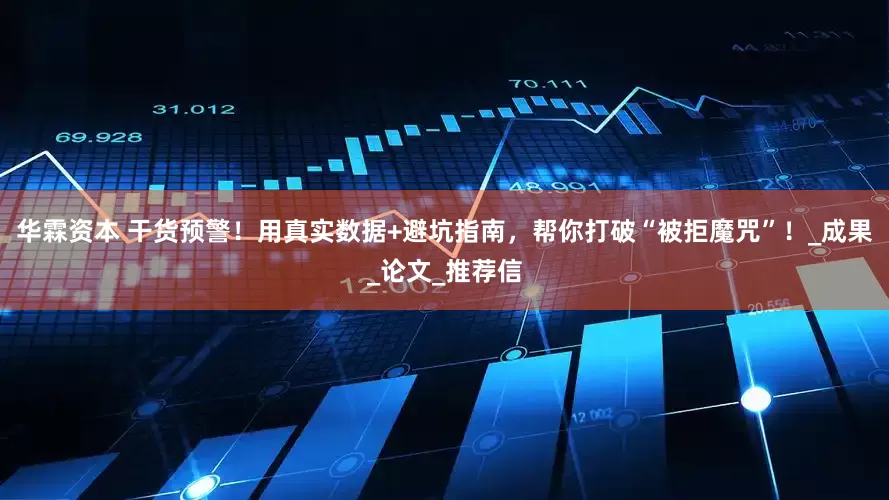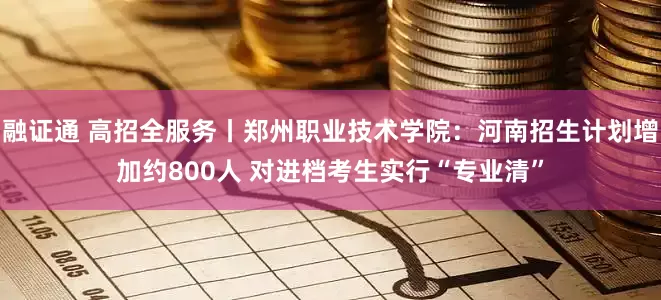“拼好团永利配资,出发!”浪浪山小妖怪拼多多式取经路上藏着每个普通人的影子
上观新闻


“他们可以取经,我们凭什么不可以?”这句从浪浪山小妖怪嘴里念出的台词,像是一种突然间的醒悟,也像是积累了很久才迸发出的呐喊,四个草根小妖似乎是在无意间承载了《西游记》这一经典IP里传统神话叙事权力的转移。
当然,这不是无意之举,而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中国奇谭》首部动画电影时,将目光投向西游宇宙的“无名之辈”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与猩猩怪,策划的一场关于“配角革命”的叙事实验。从原作中看似边缘的配角或小人物切入,挖掘其未被展现的动机、背景与成长弧线,重构一个以他们为主角的全新故事,“配角视角创作”的本质是对叙事权力的再分配。小人物被赋予主角的叙事权重时,那些曾被忽略的悲欢、挣扎与微光,可以照见故事真实的褶皱。小妖怪们不再是孙悟空金箍棒下的背景板,而是摄影机对准的主角,《浪浪山小妖怪》以平行时空策略重构西游故事,用富有“喜剧”和“旅行”的类型元素,在唐僧师徒的宏大叙事缝隙中,开辟出一条属于小人物的、具有当代意识的取经之路。监制陈廖宇称之为“《西游记》补写”——这不是改编或新编,而是在经典大英雄传奇未书写的留白处,注入当代普通人的灵魂。

叙事权力的颠覆与神话解构
传统神话中的小妖是英雄史诗的燃料与垫脚石永利配资,而《浪浪山小妖怪》的颠覆,正是将镜头对准了浪浪山生态链底层的无名者。在短片《小妖怪的夏天》中,小猪妖的“职场困境”已引发广泛共鸣——熬夜制作的箭矢被上司黑熊精随手折断,肉身被当作锅刷磨秃皮毛,长片电影延续此设定,并将其扩展为“系统性压迫”:小猪妖三年考不上大王洞“编制”,劳动成果被随意否定,好友乌鸦精因窥见机密被清理。进而,影片完成了对配角群体的主体性建构,小妖们也具有了完整的成长弧光。社恐猩猩怪被迫扮演齐天大圣;话痨黄鼠狼精强装寡言沙僧——这些“身份错位”的荒诞感下,是对“成为谁”的主动求索。
小妖精的组队与取经构成了故事的主体,这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是文化积淀的表征,也是让观众对作品具有概念感和轮廓感的敲门砖,这是传统大IP的作用。当观众进入故事的大门后需要新鲜感时,影片对西游世界的解构作为一种创新,扑面而来。黄眉大王戳破四人伪装时说了一句锥心的话:“孙悟空五百年前就认识如来,猪八戒沙僧是天神转世,唐僧是金蝉子,你以为取经是谁都能去的?”取经是普度众生的修行,也是一种世俗人情社会的晋升途径,小妖们的“冒名顶替”,可以看作是对叙事垄断权乃至某种社会特权的争夺与嘲讽——当英雄叙事被垄断,凡人只能靠扮演英雄,才能靠近自己的神话。当“冒名顶替者”成为“真实取经人”,这种对大人物的顶替,经过错位戏仿、自我否定到自我相信,变为让小人物成为更好自己的过程。小人物团队合作的心路历程,正是这样一种身心合一、从“小”到“大”的成长。

喜剧外衣与公路叙事
影片以“错位喜剧”为外衣,以“公路片”的走走停停为结构和节奏,包裹着丰富的现实指涉,以及颇有意味的存在主义内核,这些共同谱写出一曲动人的凡人歌。
四个小妖的取经之路,本质是一场冒名者的身份实验:蛤蟆精戴上头套装唐僧,小猪妖挥耙扮八戒,话痨黄鼠狼为演沙僧自我禁言,社恐猩猩怪颤抖着举起“金箍棒”——肢体与身份的极端反差制造了密集笑料。西行之路成为凡人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如猩猩怪在被迫扮演英雄的过程中,终于吼出“我是齐天大圣”的悲壮宣言。小雷音寺战役是“冒名顶替主角”(假师徒四人)与“冒名顶替对手”(假西天假佛祖)的交锋,将凡人的“冒名游戏”推向极致。
影片结局可谓是献给所有小人物的安魂曲。小猪妖命运的“干扰事件”是刷锅刷丢了印在食鼎里“大王洞”家族的“名字”,而取经四人组最终溃败于小雷音寺,记忆消失,修行归零,连“名字”都未来得及留下。弥勒佛的“呵呵”冷笑与孙悟空施舍的四根毫毛,让他们的奋斗沦为天庭眼中的荒诞喜剧。修行归零的设定具有存在主义意味:一面是宿命,一面是抗争宿命,真正的取经不在终点,而在上路本身,凡人的动人之处,恰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精神与《大闹天宫》的浪漫反抗一脉相承,却更贴近当代普通人的生命体验,这里没有翻天覆地的神通永利配资,只有在生存的缝隙中笨拙生长的勇气。
影片也将对凡人深深的温柔藏于片尾留白之中:村民们在破庙供奉四个模糊塑像,正说明凡人的神话已在民间生根。当片尾彩蛋中四个小妖以Q版形象跳起魔性舞蹈时,银幕内外响起掌声与笑声,这或许正是电影献给所有“浪浪山居民”的启示:翻越山丘可能仍是山丘,但在出发的刹那,凡人已在自己的路上成为主角。

从“浪浪山”到“打工人宇宙”
《浪浪山小妖怪》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电影文本与当代社会的互文,以及由此唤起观众的共鸣感。影片构建了多层次的互文网络,让对经典神话的解构与当代现实共振。笔者以为,这种互文性与共鸣感,表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其一,是职场隐喻。浪浪山大王洞是“体制内饭碗”,黄眉的小雷音寺则是“大厂总部”。小猪妖刷锅被斥“祖传字迹磨没”,像极了打工人奉献自己熬夜做的方案不知触碰了领导的哪片逆鳞。公鸡画师被甲方反复折磨的画像桥段是对职场甲乙方关系的夸张凝练。四个小妖的取经之路,恰似当代年轻人从“打工人”向“创业者”的冒险跃进,他们一路从草台班子搭建到攫取第一桶金,到误打误撞获取资源,再到遭遇资本巨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打压与收买,成功与否最终并无定数,既充满偶然性,也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理解成功。
其二,是网络梗文化基因。影片将“我想离开浪浪山”的爆梗升华为主题意象,网友续写“人间风雨处处有,何处不是浪浪山”成为角色的宿命注脚。官方宣传语“拼好团,出发!”以拼多多式戏谑,解构了取经的神圣性。“即见如来,为何不跪”台词一出,观众便心领神会,因为这来自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当猩猩怪高呼“我是齐天大圣”时,也与《黑神话:悟空》中“白骨之后,重走西游”形成互文,呼应了前面讲的“当英雄叙事崩塌后,凡人能否在废墟中自建神话”的主题。
其三,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自身传统的接续创新。在三维动画越来越成为市场主流的当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近乎执拗的匠心进行着民族风格的二维动画创作,《浪浪山小妖怪》1800多个镜头、2000多张场景图背后,是600余人制作团队历时四年的精心雕琢与枯坐耕耘。监制陈廖宇说:“我们不是用镜头表现笔墨,而是用国画笔墨构建电影镜头语言。”一方面,二维动画的艺术性或许才能更好地承载东方美学的写意基因,就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基因在《浪浪山小妖怪》中苏醒,中国动画的东方美学血脉在当代银幕上重新搏动。另一方面,中国动画学派需要接续创新,不论是民族风格与喜剧样式,还是“笔墨入镜”美学理念与实践。影片中小猪妖獠牙的手绘弧线、水墨氤氲的山川云气,诸如此类的细节让传统笔触在银幕空间中获得灵性与生机。但这种坚守绝非守旧,传统国画与西方透视光影融合,用工笔勾勒的角色在光影间跃动,敦煌色系的胡桃木林渲染出宗教意境等,这些东方美学元素在当代银幕完成了创新融合与基因重组。从这个意义上说,《浪浪山小妖怪》背后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新时代也具有了“浪浪山”氛围和“打工人创业”气质了。这种“反身性”在电影之外又与电影互文,同样让观众动容与思索。
希望《浪浪山小妖怪》能在这个暑期档“破圈”,这样,可以说它完成了双重意义上的“取经”:一方面,它让配角夺回叙事权,在齐天大圣的阴影下,小妖用血肉之躯撞开了一条属于凡人的取经路,从而在解构与互文中联通了当代意识;另一方面,它延续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民族风格+喜剧精神”的动画血脉并锐意进取,用四年磨一剑的匠心证明中国动画学派美学传统只要不断创新,哪怕在“三维时代”乃至AI时代,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
原标题:《“拼好团,出发!”浪浪山小妖怪拼多多式取经路上藏着每个普通人的影子》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黄玮
来源:作者:程波
兴盛网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